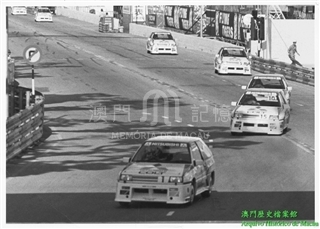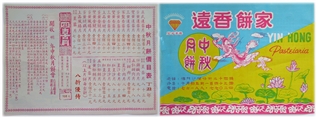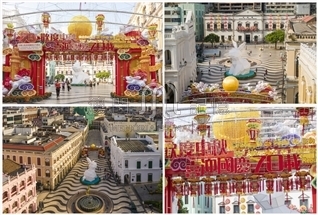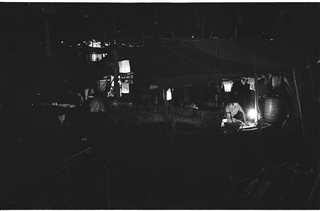為肯定市民積極參與“澳門記憶”文史網各項徵集活動,持續為平台提供豐富的圖片素材,澳門基金會推出“澳門記憶星級榮譽計劃”,透過系統的評分制度及榮譽展示方式,表揚“記憶之友”在記錄澳門、分享故事方面的積極參與。
2026年度星級榮譽榜
賀回歸26載問答遊戲得獎結果出爐!每位得獎者可獲“澳門記憶”手機座連手機掛繩套裝1份 。澳門記憶團隊已透過得獎者註冊會員時登記之流動電話號碼,以短訊形式發送得獎通知,再次感謝會員們的支持和參與!
>>立即查看得獎名單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2月28日,廣東巡撫法海抵達廣州府,隨即遵諭旨召見澳門葡萄牙人。3月3日公文傳達澳門。3月7日,澳門六名議事會代表安多尼奧·亞加喇(António de Aguíla)、巴斯瓜.羅薩、加斯巴.法蘭古、匡特.西里瓦(Quandt Silva)、瑪諾.比里(Manuel Pires)、華貓殊到達廣州,聽候法海傳遞皇帝聖旨。他們還帶來鼻煙、西洋酒等禮物送給法海。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廣東巡撫法海奏聞傳召澳門西洋人理事官轉宣諭旨謝恩情形摺》,第111頁;《康熙朝滿文奏摺全譯》第1170頁。兩書之人名標點均有錯誤。文中六人,安多尼.亞加喇為理事官,巴斯瓜.羅薩為議事會普通法官,加斯巴.法蘭古為議事會議員,瑪諾.比里為議事會書記官,瑪諾.法華朱即華貓殊的另譯,為澳門市民代表、富商。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一書中記載有八人:議事會成員巴斯瓜.羅薩,議事會理事官尼古勞.啡嗚味(Nicolau Fiumes),書記官莫拉(Manuel Pires de Moura),王室大法官加斯巴·法蘭古,華貓殊,加依奧(António de Sousa Gaio),庫尼亞·洛博(João da Cunha Lobo)和安多尼奧.亞加喇。
乾隆十八年(1753年2月3日-1754年1月22日)2月28日,白多祿等5名多明我傳教士在福安殉難後,福建傳教區僅余華籍傳教士馮文子一人支撐,為此馮文子多次向馬尼拉省會請求派遣教士增援。1752年底,馬尼拉多明我會決定派遣4名傳教士入華。西班牙人德迪我(Diego Terradillos)、鐸多明我(Domingo Castañedo)與兩位華籍會士嚴伯多祿、羅西滿遂於本日抵達澳門,在澳門停留一段時間後,分別離澳進入福建。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2, pp.423— 424;張先清:《16—18世紀西班牙多明我會士與澳門關係考》,載《澳門在天主教東進中的地位和作用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2009年11月。
同治七年(1868年1月25日─1869年2月10日)2月28日,兩廣總督瑞麟委派彭玉與澳門總督籌議設立抽收洋藥厘金總廠問題。瑞麟奏摺稱:照得粵東沿海等處,洋藥厘金,每多走私。查洋藥來自各國,屯集於香港、澳門。本部堂現擬於香港、澳門附近海口,擇要設立總廠,派委署大鵬協彭玉,會同文武員弁抽收洋藥厘金。凡各處商販到香港、澳門買受洋藥,即赴總廠報納厘金,發給印票印花。以後經過各處驗明印票印花,立即放行,均毋庸再抽厘金,以杜走漏而免紛擾。除札飭英國羅領事轉致香港總督查複辦理外,查澳門系貴國管轄,本部堂擬於果欄山設總廠抽收出口厘金,並於澳門東南路之汲水門、十字門西南之北山海口,分別派船稽查:想貴大臣熟悉此處情形,必定同心照應。現派彭副將前來與貴大臣面訂辦理,務希酌定見複,以便開辦,為此照會。Impressão Confidencial e Reservada de Documentos Respeitantes à Península de Macau e Suas Dependências, p. 2.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 2月28日,政治、文學與新聞週刊《澳門土生人報》(O Macaense)創刊。原由大眾印刷廠印刷,後改由商務印字館(Tipografia Mercantil)印刷。其出版人和主編為貢薩爾維斯‧希爾瓦(Manuel José Maria Gonçalves da Silva)。希爾瓦於1885年10月21日英年早逝,接任主編者為小若阿金‧巴士度律師,主要撰稿人有澳門土生人伯多祿‧巴爾卡 (Pedro da Barca)、哈爾特‧米勒(J. L. Hart Milner)和派特里西奧‧路斯(Patrício José da Luz)。由於撰稿人多為瞭解本地情況的澳門土生人,故文章內容頗具本地特色。該份週刊於1886年10月28日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47—48; 林玉鳳:《澳門葡文報章的發展特點》,載《澳門研究》第10期,1993年3月。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2月,署前山同知蔡國楨飭修關閘以北原廢舊卡廠,建磚屋一座,為巡捕兵丁棲止之所。新任澳督迪施華聞訊後,遂於2月28日照會兩廣總督張之洞,聲稱關閘至北山嶺一帶地方“向為局外之區”,清政府在此建卡顯然違反《光緒中葡條約》第二款的規定。不久,澳門政府則在關閘門外設一路燈,以表示葡方亦有權在這一地帶措置。4月25日,兩廣總督張之洞複照澳督迪施華稱:關閘以外應設廠卡,絕不與約內之界相涉。關閘之外新設路燈,並請按照條約,作速撤去,以免滋生事端。並稱關閘以北系中國獨管之地,關閘以南也並非盡屬葡界,三巴門以南才是葡人所居之地,將澳督之照會頂回。澳門政府轉又致電北京總理衙門,希望以中央壓地方。總理衙門複電稱葡人所言“局外之區”毫無根據,如果葡人不撤去關閘以外路燈,粵省官員亦可在關閘以內有所作為。葡人見中央與地方態度均如此強硬,遂知難而退。《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澳門總督為前山官員在關閘至北山嶺間設兵卡有違兩國和約事致兩廣總督張之洞照會》及《兩廣總督張之洞為關閘以外廠卡仍必次第舉辦事複澳門總督照會》,第395—397頁;蔡國楨輯:《澳門公牘偶存》,第65頁。
民國七年 (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2月28日,澳門政府船塢第一任廠長瑪利亞.洛佩斯 (José Maria Lopes)中尉卸任,由機械師勞爾.里亞爾 (Raul Boaventura Riar)上尉接任。洛佩斯1899年3月20日至澳門,1902年11月21日起任港務局快艇機械負責人,1912年升任政府船塢首任廠長,1914年又臨時兼任華務檢察署署長、民政局局長,這些皆為當時澳門地區公共行政當局的兩個重要職位。1915年,洛佩斯還曾作為挑選、購置港口工程和疏浚所需物資的委員會成員,被派往新加坡和上海,以便從上海港口及工程公司購置6艘大駁船並尋求1艘可滿足港口工作的拖輪。1922-1927年,再次獲任政府船塢廠長,1929年於澳門辭世。因對港務局船隻維修的重大貢獻,1904年8月8日曾獲澳督蒙丁尼路 (Martinho Pinto de Queiroz Montenegro)嘉獎。施華:《澳門政府船塢:造船和修船100年》,第20頁、第31頁及第37頁。
更多
尊敬的“澳門記憶”會員,您好!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澳門記憶”文史網的支持與信任。為持續優化會員服務品質與保障會員權益,本網站將自2025年4月28日起正式實施新版的《服務條款》。敬請各位會員詳閱修訂後之條款,有關內容可於以下查閱:
您已詳細閱讀並同意接受該等《服務條款》修訂內容。
若您對本次更新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感謝您一如既往的支持與信任,“澳門記憶”文史網將持續為您提供更安心、便捷的會員服務。
“澳門記憶”文史網 敬啟
發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使用說明
檢視全站索引
“AND”,為縮小檢索範圍,表示前後搜索項之間的 “交集”;
“OR”, 為擴大檢索範圍,表示前後搜索項之間的 “聯集”;
“NOT”,為排除不相關的檢索範圍 ,“AND NOT”表示第二個搜索項,在檢索範圍將被排除。
已經有澳門記憶帳號了? 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