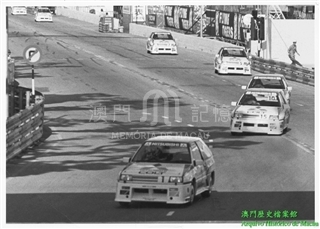為肯定市民積極參與“澳門記憶”文史網各項徵集活動,持續為平台提供豐富的圖片素材,澳門基金會推出“澳門記憶星級榮譽計劃”,透過系統的評分制度及榮譽展示方式,表揚“記憶之友”在記錄澳門、分享故事方面的積極參與。
2026年度星級榮譽榜
賀回歸26載問答遊戲得獎結果出爐!每位得獎者可獲“澳門記憶”手機座連手機掛繩套裝1份 。澳門記憶團隊已透過得獎者註冊會員時登記之流動電話號碼,以短訊形式發送得獎通知,再次感謝會員們的支持和參與!
>>立即查看得獎名單
18世紀末,在廣東、廣西沿海活動的海盜急劇增加,澳門受到中國海盜的嚴重騷擾。當時澳葡當局僅擁有兩艘武裝船,只能守衛澳門的港灣,不足以捍衛澳門附近的水域。在珠江口一帶,海盜不僅在澳門炮台射程範圍內劫掠中國商船,還打劫外國的舢舨小船,綁架外國商人。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2月14日深夜,一隊海盜直接偷襲澳門。他們自澳門半島北部登陸, 直奔東望洋山,企圖佔據可以控制全澳的東望洋山炮台。守衛炮台的士兵發現後,迅速開槍射擊,把他們趕走。1807年5月6日,由海軍少校巴雷托(Barreto)指揮下的澳門小艦隊在澳門附近海域與50艘海盜船遭遇。海盜在人數方面佔壓倒優勢,葡萄牙人則善於使用火炮、火槍。經過1小時激戰,海盜被擊敗,四處逃遁。葡萄牙人緊咬海盜頭目的大帆船不放。最後,巴雷托與30名船員跳上海盜頭目船,用劍與海盜格鬥,海盜多被砍死,其頭目也跳海自殺。這場惡戰後,海盜暫時停止了對澳門的直接騷擾,但不久又恢復了在澳門附近的活動。1809年,一艘來自果阿的葡萄牙雙桅船在澳門附近水域遇上了海盜紅旗幫的主力,該船被海盜劫獲,船長和大部份船員均被殺死,還將葡萄牙國旗在海面上拖曳,誇耀他們的勝利。不久,一艘葡萄牙快艇又被海盜船圍攻,死傷慘重。葡萄牙人急於報仇,派阿爾科弗雷多(Alcoforado)指揮兩艘武裝船出海。9月15日,與紅旗幫一支船隊相遇,雙方激戰,各自都受到很大的損失,葡船多處被擊傷,已無法繼續作戰。通過多次與海盜的較量,葡萄牙人明白單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排除海盜侵擾的。
大廟,又稱大堂,原名Se Cathedral,中國之《香山縣誌》舊稱之為望人寺、 據“祝誌”載稱:“大廟在澳東南,即望人寺。夷人始至澳所建也。”該廟在大廟頂之崗上,昔日崗前未有崇樓巨廈,阻其視線,南灣海面,可以一目瞭然,市舶出入皆得而見之也。夷婦常陟彼高崗,目盼其良人之歸也,故稱望人寺。大廟舊本澳門天主教會之中樞,嘗作為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座堂,其後座曾闢作主教之居所,但現已遷往西望洋山上耳。大廟之始建歷史,已年湮代遠,實不可攷。約在十七世紀初期,澳中已有大廟之設矣。殆經二百餘年後,風霜雨露之剝蝕,其建築日漸殘破。直至一八四九年時,天主教徒為安全計,迺即集衆捐資,從新將其改建,使成現狀。於一八五零年二月十四日,由澳門主教馬大主教Dom J.da Matta主持初祀典禮。可惜當時建築,仍是沿用木料,難以耐久。廷至一九三七年,廟貌復感頹廢,迺不得不改為三合土築。從此鐘樓對峙,十字高支,堂皇矞麗,聞是次建築費曾耗去十萬零九千元云。《澳門雜詩》中,有詠大廟者云:“大廟最始建,歲首迎耶穌,前導十字架,僧徒持咒珠。”大廟,在澳門各天主教堂中,雖非最大,所以被稱為大廟者,以奉祀之神為赫赫有名之聖彼得也。且該廟曾被視作澳中天主教之中樞,故有是稱。據傳該堂初時存有不少天主教遺物及古蹟,如大三巴寺火燒時,被教徒歷盡艱苦搶救出來之各聖人遺骨;如方濟各沙勿略之臂骨等,均曾暫供祀於大廟內。後大廟重修,迺移往三巴仔教堂保存。攷大廟之建築,富有西班牙宗教色彩。外形簡樸而純潔,內部則精巧奇趣。崇偉之祭壇下,掩埋看許多古墓,如澳中之第十二任主教俾利喇波治之靈機,亦埋葬於其間。聞俾利喇波治生前,曾為重建大廟而竭盡畢生精力云。古時天主教堂之牆壁,每有埋葬之墳墓,大都是神甫主教之遺骸,惟近來此風已變。聞數十年前,一次大風竟掀起大廟傍之一株巨榕,致大廟之傍壁為之傾倒,牆內無數白骨及骷髏頓現,後隨移葬於西洋墳場內。近讀商衍鎏探花之詩書畫集,內有詠大廟詩云:“學道三巴吳墨井,樓居望海世同危。遙聞大廟留遺畫,魚作清齋教律奇。”按大廟內尚保存有名畫多幀:如聖約翰受洗圖,及日本天主教徒在長崎被釘十字架圖,皆宗教畫中之名作也。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9月18日,澳門議事公局向總督吉馬良士請求,准許發行一次彩票,籌集維持議事公局小學的辦學經費。20日,澳門議事公局獲批准每年可發行一次彩票,以籌集維持所辦小學的經費。據《華友西報》1853年2月14日刊登澳門彩票廣告可知,澳門彩票設計的目的是將贏利的15%扣除交政府司庫作為公共工程的費用。每張彩票為2西班牙元,1元可以購得半份。彩票的批准發行,由澳門地區大法官塞克拉‧品篤、指揮宮佩得羅‧布伊(António Pedro Buys)和管理華人事務宮勞倫索‧馬葵士簽署。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41;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4頁;The Friend of China, February 23rd, 1853; Vol. 12, No. 16, p. 62.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2月11日,法國青年旅行家王室貴族盧德維奇‧德‧波瓦(Ludovic de Beauvoir)公爵與龐蒂埃弗爾公爵(Due de Penthièvre)一起周遊世界。兩人於1866年4月啟程,經澳大利亞、爪哇島、暹羅、香港,於本日抵達澳門。到澳門後,受到澳門政府的熱情款待,為方便他們遊覽,澳督柯打為他們提供了一艘小艇,他們得以游遍當地名勝,如南灣、望廈、議事公局、炮台、教堂及網球場,還參觀了賈梅士洞。14日離開澳門。盧德維奇回國後,相繼出版了兩部遊記,其中一部為《爪哇、暹羅與廣州》,該書的第13章即其所見的澳門:經過三個半小時的航程,我們也就到了氹仔錨地附近。借著夕陽餘暉,澳門半島映入眼簾。葡萄牙國旗在建在陡峭懸崖上的要塞上空飄揚。這陡峭懸崖總有七八處之多。懸崖上方是用紅花崗岩堆砌而成的雉牒。光禿禿的山頭一個接著一個,高出海平面兩百來米。屋頂呈南國式平台的房屋鱗次櫛比,有的漆成藍色,有的漆成綠色,有的漆成紅色。教堂鐘樓共有十來個。每幢房屋窗戶都裝著鐵條。城內各個街區呈圓錐狀,一條條僅有兩米寬的小巷都鋪著方磚。山城腳下是一個半圓形的港灣,停泊著幾千條小木船。我們上岸,碼頭上擠滿苦力。沿山勢而建的“高樓斜巷”(Calçada de Bom Jesus)和“巴掌圍斜巷”(Travessas do São Agostinho),帶有典型的葡萄牙特色,狹窄的街道兩旁是用花崗岩砌成的平房,看上去酷似一座座監獄。被征服者佔據的這座城市,居民成分相當混雜。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de Albuquerque)的後裔,有的挎著戰刀,有的脖子上圍著圍巾,走在街上成群結隊,步履迅疾。他們是葡萄牙人和中國人的混血兒,而那些中國人原來已帶有馬來人、印度人和黑人的混雜血統。總之,他們身材矮小,顯得相當瘦弱。淺褐色的臉膛上,長著兩隻大大的杏仁眼。他們就生活在這半基督教半巫術,也即半文明半亞洲型的社會中!城裡有兩家英美式小旅館。我們在昏暗的小巷裡走了很久,總算在其中一家找了個棲宿之地。旅館好似一座沒有窗戶的穀倉,不但潮濕,而且臭氣熏天。難以數計的蟑螂已先我們一步,在這裡安營紮寨。我們住的地方實在惡劣透頂,為了避免蟲蟻的騷擾,我們讓旅館老闆給找了個中國苦力,帶我們去演中國戲的地方看看。這些戲場是該城唯一的消遣去處。山城的每一條街,都要爬上爬下。石頭階梯旁標有本街道名字的告示牌。後來,我們總算進到一幢喧鬧不已的木頭房子裡。大廳兩邊擺著一排小桌,每桌坐了四個中國人。他們正在那裡吃著、喝著,有的還抽著煙。我們在前排找位置坐下。舞台上正在演出插入雜耍的戲。這場戲自上午10時開場,現仍在繼續中。可是,由於聲音嘈雜,我們捂住耳朵,這場耐人尋味的戲剛看了約一小時,戲場裡忽然一陣騷動,桌椅板凳被打翻在地,一幫人從門外擁進來。場內人紛紛給他們讓道。進來的幾位不速之客中,有幾位是總督的副官,還有一位是輕型巡洋艦艦長。他們全都穿著正式的禮服,帽子上插著羽飾,胸前掛滿勳章。這個陣勢自然非同尋常。由於戲場裡只有我們兩個歐洲人,穿著又非常隨便,場內的中國觀眾隨即交頭接耳,甚至大聲鼓噪,斷定這些人定是來抓我們的。不料卻見這幾位先生十分謙恭地走到公爵面前,向他轉達了總督的問候,邀請他住總督府。雙方約定,明天中午去拜訪總督。考慮到一旦進入總督府,我們作為一個旅行家將難以再有什麼真正的發現,為了利用在澳門最後一點自由的時光,我們帶著那位苦力,又到了中國人所聚居的街區。這裡環境整潔,茫茫黑夜中點著的各色燈籠,十分迷人。該城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賭場,因為澳門有“天朝的摩納哥”之稱。海南、廣東和福建的中國富人常會不惜一切地跑到這兒來,在“三十和四十點”賭局(此賭法在他們的家鄉是禁止的)上,把錢輸得精光。主持賭局的莊家是一位年已花甲的老者,銀白的辮子垂於腦後,指甲留得很長,幾根稀疏的鬍鬚閃閃發亮。四周下注的賭客竟達幾百人之多。時近午夜。只見那些中國人身上穿著絲綢,走在路上,每人都提著個大紙燈籠,樣子很是奇特。我們對自己今晚這趟賭場之行深感滿意,於是讓身邊那個苦力帶我們回到那家蟑螂成群的旅館。第二天上午,由總督副官唐‧歐索里奧(Don Osório)陪同;下午由原任炮兵軍官的柯打總督本人陪同,遊覽了澳門市容。這其實無須費多少時間,因為整個領地看來只有5公里長,2公里寬。小小半島完全像是一個人的腳印,後跟向著海面。大腳趾與另一個400公尺寬的狹長半島接壤,因而與香山大島連成一體。後跟部分由9座岩石遍佈的山嶺組成,山下就是燒灰爐炮台、媽閣炮台、聖若奧(São João)堡壘和雀仔園(Forte de S. Jerónimo)炮台。腳板底長長的內曲線地帶,是中國人居住區,有房屋12. 5萬間(此處應理解為12. 5萬人,此處人口資料明顯誇大,當時澳門華人人口應為6萬—7萬人)。2000餘葡萄牙人則住在另一側曲線的外延地帶。“南灣”即濱海空地,是其繁華幹道。裝有鐵門的宅第、總督官邸、警察局、政府機關和商店都集中於這條幹道上。五顏六色的拱形建築和一座座修道院呈現出濃厚的葡萄牙風情。腳背像是一堵由低而高的圍牆,把兩個居住區截然隔開。其他幾個腳趾則像是突然蜷縮而翹了起來,形成一長條拔地而起的高山峻嶺。山上有嘉思欄炮台、東望洋炮台和大三巴炮台。此外還有七八座規模稍次的炮台。城外是阡陌縱橫的菜畦及望廈村。一道16英尺高的鐵絲網,把這塊殖民地同中國大陸隔了開來。我們走的大路是沿山腰石壁開鑿出來的,風景十分優美。百餘座大口徑火炮,捍衛著半島四周的海域,並可在12. 5萬條“辮子”所住街區一旦出現反叛,便向那裡轟擊。接著我們參觀了南邊的“大堂前地”(Praça da sé)的大教堂和議事公局。在議事公局的門上,自1654年以來便掛著一塊匾額:上帝聖名之城無比之忠誠(CIDADE DO NOME DE DEUS. NÃO HÁ OUTRA MAIS LEAL)。我們還去各兵營、修道院、聖保祿教堂、“窮人收容所”(Asilo dos Pobres)等處,走馬觀花地看了看。聖保祿教堂是1594年由耶穌會教士修建的,今已大部被火焚毀。這些古代教會建築,鐘樓上豎有十字架,壁龕裡繪著聖人畫像。至於大幅壁畫,更是趣味橫生。除此之外,你還可看到,婦女臉上都罩著面紗,頭戴橢圓形黑帽的修士則在那裡慢慢地走著,另有一些戴著白色圓帽的修女,在忙著賑濟窮人。下午3時,幾條彩旗飄揚的小船載著我們穿行於數百條喧鬧不已的木船間,把我們送上“卡洛斯王子”(Príncipe Carlos)號炮艦。大家在炮艦上喝了幾杯酒,祝“皇家海軍”(L'Armada)一切順利。隨後,我們棄舟登岸,沿著濱海林蔭道驅車前行。傍晚我們到了賈梅士洞穴。洞穴地勢偏僻,荒無人煙,四周是巨石。遺憾的是,當地市政官員卻將這富於詩意的莊嚴肅穆的場所給白白糟蹋,因為他們在這名垂青史、供後人憑弔並給以眾多啟迪的地方,建了一個很俗氣的書亭。書亭外側亂糟糟地張貼著一些詩文,裡邊放著一尊樣子非常滑稽的半身塑像。人們從中看不到一點詩人當年慘遭放逐,但仍心向祖國的博大情懷。一位法國詩人也曾遭流放,來到這荒僻的角落。有感於同樣不幸身世,他曾命筆在洞穴北面的石壁上寫下這樣幾個字:“教會詩人路易‧里安濟(Louis Rienzi)於1827年3月30日來此憑弔。”隨後,我們策馬揚鞭,在山上飛奔一程,很快來到山下的望廈村。村內一座寶塔,遠看很是不錯,及至走到跟前,卻覺得並不怎樣。廟裡的和尚對前來觀光的客人是要討賞的。且這兒還有一怪,由於本地成為殖民地已很有年頭,不但中國人已相當地葡化,葡人也已相當地漢化。比如這些和尚口中的菩薩,如今已用的是我們那些聖人的名字。因此在那些三頭六臂、膀大腰圓的菩薩中,叫“聖法蘭西斯科”或“聖奧古斯丁”者比比皆是。第三天,我們去對澳門的熱門行當——從事販人的“豬仔館”(又稱“巴拉坑Barracons”)——作了番詳細調查。我們進的第一家人販商店,外表十分高雅。門前鮮花簇簇,兩旁點綴著大型中國瓷瓶。客廳裡擺放著名貴的傢俱。不過這是接待官員的地方,拐角處一張辦公桌上堆著一摞業已翻爛的大本帳簿。因此,一切看來似乎都非常美好。然而在同皮膚黝黑的店主寒暄幾句後,我們很快發現左右兩邊的長長過道裡,一個個“庫房”已裝滿“即將移民”的中國人。他們被集中在那裡,正在等待啟程,但個個面色慘白,神色悽惶,其衣著襤褸蓬首垢面,顯示出他們是生活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中。這販賣中國人的交易實在是一部催人淚下的歷史。此交易自開始至今雖然還只有19年,但為獲得所需“貨物”,人們是展開了多麼可怕的殺戮,進行了多麼無恥的投機,因此此交易比它所取代的黑奴買賣還要殘酷千倍!每一筆買賣都意味著不知犧牲了多少無辜!澳門每年約有5000華工前往哈瓦那,8000華工前往卡亞俄(Ca-llao)。如果移民由正直無私的機構負責辦理,這對食物匱乏或勞工不足的國家無疑都是一大好事,應該十分感激這些救急救難的船隻幫助因土地貧瘠而養不活全體居民的中國卸脫過重的人口包袱。但是,那就首先不能讓強盜、騙子從中插手,使此事打上無法抹掉的罪惡胎記。毛病的根子就在於成千上萬的苦力是被硬拉或誘騙而來的,事後在澳門追問他們是否出於自願,純屬多此一舉。就算他們作出正面的答覆,那又能夠說明什麼問題?一旦受騙負債,落入募工者的魔爪,這些可憐的人便被送到債主的巴拉坑,募工者與帝國官吏簽訂協約,前者每送一名華工可得40—50法郎;後者從中抽取小費。因而,當葡萄牙巡視員問及華工是否自願時,他們也就不得不以謊言搪塞。他們知道,如果拒絕出海,債主、掮客和官吏全都饒不了他們,會對他們進行無情的報復;他們走投無路,恐懼不安,饑腸轆轆,備受折磨,幾乎必定還會落到挨打遭罪的境地。總之,只要中了第一個圈套以後,厄運便接踵而來。從事拐賣人口的掮客每交出一名華工可得50法郎,賣身者自己得300法郎。我們曾去一個巴拉坑看過,其主人是帶一半黑人血統的葡萄牙人,他今天就從來自廣東、廣西和湖南的掮客手裡取得上百名苦力,總共付出3萬法郎。這名巴拉坑主十足是一副人販子的模樣:肥胖、五短身材,扁平的鼻子,兇狠的雙眼,雜亂的鬍子,手裡還拿著一根粗大的喪命棍,這自然是用來對付奴隸的了。在把苦力送進艙底之前,巴拉坑主必須先讓他們在葡萄牙管理華人事務官面前列隊甄別,然後再與船主拍板成交。正是在這時候,政府才開始履行職責,現行法規才開始發揮作用。惡有惡報。販賣華工既是一本萬利的大生意,使用欺騙和強暴的手段似乎在所難免,可是在執行新法律以後,這些手段就成了增加開支和減少收益的原因。當華工在殖民當局問他們究竟願意返回中國或出洋去哈瓦那時,1000人中往往總有200人鼓起勇氣,不顧巴拉坑主報復的危險,拒絕出洋。如果不進行殘酷的報復,出錢收買、運送和養活苦力的巴拉坑主們豈不因苦力的臨時變卦,讓開支的費用全部泡湯!經當局派員核實後,同意出洋的華工又返回巴拉坑。新法律禁止他們在6天之內外出,在此期間,殖民當局再次派員甄別,並對苦力說:“請拿定主意,你們還是自由的!”苦力們在船隻起錨前往往要等待一二個月,他們在落船前還要經過兩次甄別,公開表明他們完全出於自願。地方當局在等待期間要求進行視察和調查,這固然值得給予高度讚揚,但應該肯定,苦力受到商人的控制越來越緊,他想脫身的可能也就越少。因為他寄人籬下,還欠著無從清償的債務!如果他在白吃白住兩個月後聲稱:“我不願出洋!”那該遭受怎樣的對待?他就必須先向為他提供吃住的巴拉坑主付清欠帳。船隻終於整裝待發,即將起錨,莊嚴的時刻馬上就要到來了!就在出發的前一天,賣身契在管理華人事務官面前當場簽字。苦力們陸續上船,巴拉坑主以每人約750法郎的價格把苦力賣給西班牙航運局的代表。經對我們的夥伴再三詢問後,我們終於對賣身契的內容有所瞭解,契約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寫成,由應募華工、皇家檢察官和西班牙領事簽字畫押,其主要條款敘述如下:“我許諾為本契約持有人服役8年,每天工作12小時,並放棄在此期間的一切自由。我的雇主答應每月給我4皮亞斯特(20法郎),有飯吃,有衣穿,並在契約期滿之日讓我自由。”從澳門的巴拉坑到古巴的甘蔗種植園或鳥糞採集地,苦力的身價也從300法郎漲達1750法郎,這筆差價由經手人平分,就是說,募工者得50法郎,巴拉坑主得400法郎,船主得500法郎,當地的售主得500法郎。看到這些臉色蒼白衣衫襤褸的可憐蟲橫七豎八地躺在巴拉坑裡,我真感到有說不盡的心酸。唐‧歐索里奧領我們看了附近的幾所花園洋房,我完全知道,它們的主人20年前曾作為苦力外出,如今已經衣錦回鄉!我完全知道,苦工們如果在8年當牛做馬期間,能經受住每天12小時強迫勞動的折磨,在棍棒的驅使下搬運鳥糞,他們隨後可能發財致富,因為在獲得自由以後,他們的勞動報酬十分可觀!但在這些被半拉半騙地塞進船艙冒死出洋的成千上萬名華工中,究竟有多少人能衣錦回鄉?招募華工是19世紀最有利可圖的活動之一,經營此業“先生們”從每一名苦力身上大約可得l400法郎,在我看來,他們的行徑與海盜無異,只是裝扮成“道貌岸然”而已。香港的英國殖民當局率先明令禁止在其陸地和海域從事“苦力移民”,我對此感到由衷的欣慰。港英當局已隱約覺察,苦力們在中國蒙受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之苦必定比他們離鄉背井所受的苦難有過之而無不及。澳門的情形比較微妙,猶如吸附在中國巨人身上的螞蟥,這個水陸碼頭的基本構架始終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澳門不全歸葡萄牙人統治,又不全是華人作主,既不信奉基督,又不信奉菩薩。葡萄牙總督與盤根錯節的舊官僚勢均力敵,有時偏向我們歐洲在遠東的政策,有時又對來自廣州和北京的威脅誠惶誠恐和束手無策。只是經過亞馬留的努力整頓,澳門的地位才算真正確定,但葡華混雜留下的爛攤子卻不是一下子就能收拾乾淨的。我們離開巴拉坑不到五分鐘,正氣喘吁吁地沿著“聖母瑪利亞斜巷”(Calçada da Buenita Maria Virgem)拾級上行,街面鋪著光滑的石子,兩側排列著整齊的綠色小屋,裝有柵欄的窗戶像是監獄的氣孔。這時突然見到前方有一個年輕的華人,死命拉住管理華人事務官的坐轎,號啕大哭。我們對“閣下”(這裡對所有人都稱閣下,包括我在內)行禮後就問,頸上套著號牌的那個僕人為何哭得如此傷心可憐。這位大人身穿官服,正從市政廳打道回府,剛在那裡簽發了700名苦力的契約,苦力們次日即可出洋。可是,眼前這名可憐青年不滿18歲,根據法律,他的申請遭到拒絕。落選者跪在管理華人事務官面前,不斷苦苦哀求,有人把他的話翻譯給我們聽:“他求大人讓他出洋,如果把他退了回去,出錢買他的主人就丟了利潤,他會因此受到最惡劣的對待。”可憐的孩子,居然因別人不讓他出洋去挖鳥糞,就此斷了一切生路!澳門約有華人12. 5萬名,葡人2000名。1865年出港的船隻已從30年前的1000次下降到206次;貿易幾乎僅限於進口鴉片7500箱(價值1631萬法郎)和出口茶葉(340萬法郎)。正如你們可以想到的,澳門的所有捐稅全由華人負擔,不論他們是常住的或暫住的。亞洲民族的一大致命傷是從其惡習嗜好抽取最多油水。50萬法郎來自賭場;30萬法郎來自鴉片和販賣人口的巴拉坑!這在118. 8萬預算收入中占了相當的比重。至於支出,澳門官員俸祿不高,僅達97. 3萬法郎,餘下21. 5萬法郎上交葡萄牙國庫,據說國庫隨時可供這些收益存放。盧德維奇的遊記以中葡兩國之外的第三者立場十分客觀地記錄了l9世紀60年代的澳門,特別是對澳門華人生活及葡萄牙人賣豬仔之活動進行了真實的描繪,給我們留下了這一時代其他檔案文獻不可能記錄的且十分珍貴的細節,作者十分痛恨“美其名曰為苦力移民牽線搭橋”而公開進行的人口販賣勾當,並對此行為展開無情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描述的望廈村的寶塔及村裡中國人的葡化,這是其他文獻所未見載者。據德立‧龍巴(Denys Lombard)的介紹,他們遊覽澳門時,見到了澳門的網球場,這應是網球傳於澳門的最早記錄。德立‧龍巴(Denys Lombard)著,李長森譯:《德‧波瓦公爵在澳門:1867年2月》,載《文化雜誌》第23期,1995年。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20日,澳門公物會與玉生(Ioc-Sang)、枝山(Chi-San)訂立承接供辦牛肉之合同,以一年為期,係自7月26日起,擔保人為順合劉田。向來澳門發賣牛肉,皆是在公物會招人承充。上年2月14日,澳督發佈第42號之札諭,禁止在公物會承充販賣牛肉。該年5月11日,奉到第30號上諭批准。不料,施行以來,澳門所賣牛肉顯有不敷日用及價昂不佳,以致澳門商民聯稟僉稱街市販賣牛肉諸多掣肘,民人日久受屈不少,懇速設法以除此害。據查販牛來澳,實因艱難,是以舊承充人幾於包攬,似有壟斷生意,從中作梗,以致供辦極少。澳門政府不得不重新招人承接供辦牛肉。《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8月20日第32號,第281-282頁;《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7月13日第27號第一附報,第228-229頁。
《知新報》第一百一十二期刊登《廢立要聞彙錄》、《廣州灣劃界條約》、《日人論湖南通商》、《美國金山大埠保救大清皇帝會章程》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2月14日,先是上年郵傳部飭令原辦廣澳鐵路職商梁雲逵迅速回籍招集商股,一經外務部與葡使商妥後,即行開辦廣澳鐵路。梁雲逵遂於當年陰曆四月間親往天津、漢口、上海、香港、廣州等商埠,聯合創辦同人實力招股,認股者極為踴躍,至八月始回京待命。無奈遷延至今,未獲任何諭令,恐葡人另生枝節,且股友懷疑,漸成渙散。為此梁雲逵是日呈請郵傳部,要求先由廣州省城築至香山縣城,約合170餘華里,待郵傳部與葡使商妥後,再照原案築至關閘。此議後獲准,但未能執行。《香山明清檔案輯錄》4《外事》之《原辦廣澳鐵路職商梁雲逵等為請諮郵傳部札飭開辦廣澳鐵路事致外務部呈文》(1911年2月14日),第599頁。
更多
尊敬的“澳門記憶”會員,您好!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澳門記憶”文史網的支持與信任。為持續優化會員服務品質與保障會員權益,本網站將自2025年4月28日起正式實施新版的《服務條款》。敬請各位會員詳閱修訂後之條款,有關內容可於以下查閱:
您已詳細閱讀並同意接受該等《服務條款》修訂內容。
若您對本次更新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感謝您一如既往的支持與信任,“澳門記憶”文史網將持續為您提供更安心、便捷的會員服務。
“澳門記憶”文史網 敬啟
發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使用說明
檢視全站索引
“AND”,為縮小檢索範圍,表示前後搜索項之間的 “交集”;
“OR”, 為擴大檢索範圍,表示前後搜索項之間的 “聯集”;
“NOT”,為排除不相關的檢索範圍 ,“AND NOT”表示第二個搜索項,在檢索範圍將被排除。
已經有澳門記憶帳號了? 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