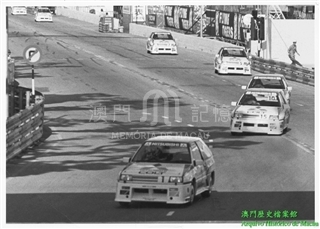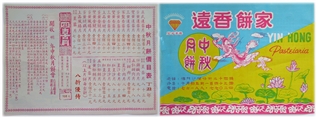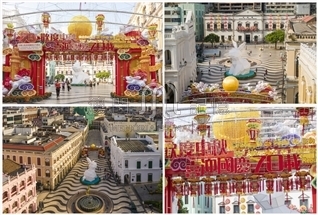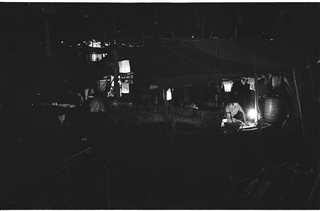為肯定市民積極參與“澳門記憶”文史網各項徵集活動,持續為平台提供豐富的圖片素材,澳門基金會推出“澳門記憶星級榮譽計劃”,透過系統的評分制度及榮譽展示方式,表揚“記憶之友”在記錄澳門、分享故事方面的積極參與。
2026年度星級榮譽榜
賀回歸26載問答遊戲得獎結果出爐!每位得獎者可獲“澳門記憶”手機座連手機掛繩套裝1份 。澳門記憶團隊已透過得獎者註冊會員時登記之流動電話號碼,以短訊形式發送得獎通知,再次感謝會員們的支持和參與!
>>立即查看得獎名單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2月2日,北京及廣東諸大臣向皇帝上疏,說葡萄牙人借行商之名窺探中華大地,然後圖謀武裝入侵。凡他們涉足之處無不以此種方式掠奪他人土地,入印度、占滿刺加均用此法,因此不宜允許他們進入中國的任何地方。針對葡萄牙人在東涌的野蠻行徑,朝臣紛紛疏言,請將葡萄牙人及船隻驅逐出澳。其中,監察御史丘道隆言:“滿刺加,朝貢詔封之國,而佛郎機拼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賞,於義決不可許。請卻其貢獻,明示順逆,使歸還滿刺加疆土之後,方許朝貢,倘或執迷不悛,雖外夷不煩兵力,亦必檄尋諸蕃聲罪致討,庶幾大義以明。”御史何鰲亦言:“佛郎機最號凶詐,兵械比諸夷獨精。前年駕大舶突進廣東省下,銃炮之聲震動城郭。留驛者違禁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私舶往來貿易,勢必至於爭鬥而殺傷,南方之禍殆無極矣。”大臣們的阻撓,也是明武宗不接見托梅•皮雷斯的原因。《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6篇第1章,第146頁。《明武宗實錄》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條。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12《雜論》。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1月21日─1567年2月8日)2月2日,教宗敕令,命埃塞俄比亞教區主教安德雷亞斯•奧維埃多 (Andreas de Oviedo)赴中國與日本傳教,並擔任該教區主教。又命第一副主教賈尼勞協助。安德雷亞斯•奧維埃多主教拒絕任命,而當時在果阿患病的副主教賈尼勞無事可做,遂以賈尼勞副主教署理。但直到1567年秋,賈尼勞才在馬六甲收到教宗的小敕書,由於不清楚大主教安德雷亞斯•奧維埃多的想法,不敢擅自行動的賈尼勞聽從醫生的建議以身患嚴重哮喘病為由,又滯留馬六甲半年,才於1568年赴澳門任。H. チ一スリク:《キリシタン時代にぉける司教問題》,第381—382頁及第378—379頁。 (後面徵引《キリシタン時代にぉける司教問題》一書資料,均出自戚印平的《遠東耶穌會史研究》一書,不再作說明。)戚印平:《遠東耶穌會史研究》第11章《16至17世紀遠東主教問題》,第480—481頁。
萬曆八年(1580年1月16日─1581年2月3日)2月2日,聖方濟各天使聖母修院(Nossa Senhora dos Anjos da Prociúncula)及聖堂在澳門南灣(Praia Grande)附近的小山上建立,這是澳門第五座教堂。其創始人為佩德羅•阿爾法羅。中國人後稱其為“噶斯欄(嘉思欄)廟”,在澳城東隅。嘉思欄,當即西班牙語Castillas或葡語Castela,漢籍中稱作“干係臘”,利瑪竇《坤輿全圖》稱“加西郎”,即指西班牙。黛烏斯(Jacinto de Deus)《植物與鮮花的樂園》記載:修道院位於城東一片美麗沙灘起始處的小山上,海浪拍打著修道院的圍牆,修道院東面和北面朝向大海。修士們在院內開辦了一所學院(Colégio),有20個青少年在裡面受教育,他們有的是正在改變信仰的信徒子女,有的是基督徒子女,在天主教義的良好薰陶下,他們將成為當地的傳道員。他們還用大量的時間學習中文,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將來可以重返廣州城。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415—416.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金國平:《嘉思欄名稱溯源》,載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第257—260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406.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7月2日,華籍世俗神父楊執德(Étienne Laforest)和高仁(Aloys Kao)在洛里昂(Lorient)乘船抵達澳門。楊執德,字德望,高仁又稱高類斯,俱北京人。先在蔣友仁(Michel Benoist)神父引領下在北京進修。1751年,兩人被保送去法國拉弗萊歇(La Flèche)公學深造,攻讀法文、拉丁文和人類學。1759年,入耶穌會,並在路易公學專攻神學。耶穌會解散後,他們在遣使會修院最後完成學業。法國國務大臣佩爾丁(Peletier)先生允諾充當他倆的保護人。1764年,又在法國科學院普禮遜(Brisson)和卡德特(Cadet)兩位院士指導下,從事物理、自然史及化學多項研究,他們學會了硝酸製版印刷法,並參觀了里昂的絲綢紡織廠、金銀器皿製造廠和火器製造廠,最後他們帶著法國王室贈送的禮品,其中有一架輕便的印刷機,以及國務大臣佩爾丁的贈言前往中國。兩人抵達澳門後,在澳門居停27天,於7月29日到廣州,翌年2月2日到達北京。榮振華(Joseph Dehergne):《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749─750頁;費賴之:《明清時期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第1141─1142頁。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2月2日,澳門總督柯打宣佈,考慮到仁慈堂收容遺棄女嬰對社會風俗有害無利,禁止再從事此類善舉,並拆除孤兒院收置嬰兒的櫃子。數字顯示,1857年1月1日,仁慈堂收容45個棄嬰,1866年12月31日時達到107個,10年間收容總數為2286名。負責研究論證仁慈堂設立之必要性的委員會主席洛佩斯‧席爾瓦在他的報告中說:“棄嬰死亡率之高十分少見,10年中死亡嬰兒占95. 5﹪,幾乎全部是中國兒童。”總督新法令於當年2月8日生效。至此,仁慈堂只負責照料此前已收容的嬰幼兒。然而法令並不能改變現實,櫃子雖被取消,但仍有很多棄嬰被拋棄在仁慈堂大門口,後者亦不得不收容他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66頁。
民國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2月2日,“聯合兄弟有限公司”又一間影院—平安戲院在新馬路正式開業,結束了國華影院一統天下的局面。該戲院初名“卡爾登戲院”,由地開張幾個月後,多次出事,風雲先生建議改名,於是遂改名為“平安戲院”。該戲院樓高4層,共有座位1038個,為澳門第一座“現代電影院”。首演片為西片《風流寡婦》 (Merry Widow)。由於域多利影院關閉,平安戲院成為米高梅 (MGM)公司、聯美 (United Artists)公司和派拉蒙 (Paramount)公司電影的獨家代理商。後因音響設備太差,無法與國華影院相抗衡。《澳門政府憲報》1936年9月12日第37號;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 (1932—1936)》,載《文化雜誌》第23期1995年;金豐居士:《二戰時堅持放愛國電影的平安戲院》,載《新報》2007年3月22日。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2月2日,日本駐澳門領事館首任領事福井保光 (ふくぃゃすみつ)、書記官朝比奈泰暉於松山做完早操返回領事館途中在連勝馬路遭到兩名華人刺殺,福井身中兩槍,重傷,朝比奈中一槍。兩人隨之被急送政府醫院,但因傷勢嚴重,福井於次日死亡。事發後,澳門政府密切配合,全力偵察,但始終沒能掌握案件的具體隱情與重大線索。葡萄牙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恩里克‧瓜雷斯馬 (Henrique da Guerra Quaresma)也為此親自前往日本駐里斯本公使館致歉。福井死後,日本外務省立即派出廣東大使館事務所領事岩井英一 (ぃちぃぇぃぃち)赴澳門出任領事一職,並准許了岩井所謂以孫嘉華為首的10位廣州青年組成的衛隊同赴澳門的請求。岩井2月內抵澳,5月離任,衛隊增至50人。岩井原籍愛知縣名古屋市中區東田町,1899年10月生於愛知縣愛知郡中村大字稻葉地。1921年畢業於東亞同文書院,漢語十分流利。岩井來澳後,重點處理福井被刺案,並經請示外務省同意,提出四點解決方案: (1)逮捕犯人; (2)總督有責任維持治安; (3)對死傷者予以賠償; (4)對日本人的安全今後予以保障。同時,岩井支持南京日本軍司令部以保護僑民為名佔領澳門的建議,不過最終因缺乏具體實施的步驟不了了之。但日軍還是從廣東對澳門實行了懲罰性的封鎖,後在日本駐葡萄牙公使森島守人 (もりしまもりと)的建議下才予以取消,造成了澳門的食糧短缺,以致街有餓殍。《西南日報》1945年2月19日《岩井英一氏繼任日駐澳門領事》;葡萄牙國家檔案館薩拉查檔 (Arquivo Salazar),Aos\CO\UE10APT4,轉引自金國平、吳志良:《抗戰時期澳門未淪陷之謎》,載《鏡海飄渺》,第153頁;房建昌:《從日本駐澳門領事館檔案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在澳門的活動》,載《廣東文史》第4期,1998年;房建昌:《有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外交與特工人員在澳門活動的幾點補正》,載《民國檔案》第4期,1999年。房建昌據日本駐澳門領事館檔稱,兩人遇刺是2月3日早上,福井當場斃命,朝比被擊穿腹部。
鄭彼岸,又名鄭岸父,號伯瑜,香山縣濠頭鄉(今屬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濠頭村)人。同盟會會員、革命家、史學家、詩人。 少年時代,彼岸有神童之譽,參加童試中獲得秀才第一名,後放棄功名,赴日本留學;相遇孫中山並接受其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在日本時開始信仰無政府主義。 1906年,彼岸與林君復等奉孫中山之命開展活動,負責策劃香山起義。1908年,他和李憐庵等辦《香山旬報》,宣傳民主革命思想,以文聲討清王朝。[1] 1910年,彼岸與林君復受命在澳門設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積極吸收會員,擴大組織,並做從廣州調駐前山的新軍和前山邊防軍的官兵的思想工作。在澳門,彼岸和林君復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2][3] 1911年,彼岸回到香山策動城鄉兵勇和組織群眾接應起義。農曆九月十六日,香山縣回應武昌的武裝起義,他身先士卒,率領革命武裝入城奪取政權。光復縣城後,他和林君復共同率領香軍支援廣州起義,受到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廣東都督府委任彼岸為香山縣第一任縣長,但他無意仕途,婉言辭絕。龍濟光禍害粵時,1914年,彼岸因受到廣東都督府通緝,逃往美洲,漂泊20多年。期間,他做店員、報販、酒家傭工等職業,自食其力;當教師時,向華僑子弟灌輸祖國文化。在加拿大,因組織華人工黨,維護僑工利益,他被驅逐出境。 1937年春,中山縣長楊子毅深知彼岸學識淵博,精通古學,治學嚴謹,特邀請他回國主編修《中山縣志》。彼岸回到濠頭村居住,並執教於鄉,藉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不及一年,日寇入侵,中山淪陷,彼岸遷居香港,修志暫擱。不久,香港也淪陷。彼岸回鄉與族人創辦五峰中學,並任教職。因籌集經費困難,薪金不足以糊口。當時,嶺南大學澳門分校想聘彼岸為教授,但他為了堅持辦好五峰中學,沒有答應,放棄月薪500元葡幣的職位。 因辦學和負責文獻會工作,彼岸認識一批青年,他經常不辭勞苦幫他們找工作,對有才幹的青年更是關懷備至,引導他們不斷進步,從而受到青年們尊崇和愛戴。 1946年初,一位與彼岸共事半年的青年共產黨員雲,在五桂山區被前來掃蕩的國民黨反動軍隊逮捕。彼岸與他共事期間,因信仰不同發生過思想交鋒,使彼岸認識馬克思主義、瞭解到馬克思主義者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 為了營救這位青年出獄,彼岸經常冒著大暑天從鄉下跑到石岐。事情不能馬上解決,雲妻不時背著六七個月的孩子來到彼岸家打聽消息。當彼岸知道她生活困難時,叫家人把抽屜裡的錢盡數給了她。後經彼岸多方努力,親自作保把雲救出牢獄,並聘請他在剛成立的修志處工作。在當時“匪”與“戡亂”的關頭,彼岸冒著極大的風險,救過兩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誣控的徐桂,另一位是劉思復。 1940年,簡又文、葉恭綽等在香港般咸道馮平山圖書館舉辦一個“廣東文物展覽會”。主持人標榜展覽會的主旨是“研究鄉邦文獻發揚民族精神”。當時,彼岸避居香港,參觀後,他立刻指出該會有50多件展品有違民族精神,乃以“寶筏”筆名,撰寫一篇題為《評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風》第100期發表。簡又文立即撰文展開論辯。 彼岸繼續在《宇宙風》發表第二篇文章。兩文旁徵博引,史料豐富,證據充分有力,論證詳博;特別是對邑人何吾騶、伍瑞隆的投降問題,他研究過20種史籍,在文中就何吾騶降清列舉大量史實,進行無可置辯的考證和論斷,使人為之折服。 彼岸兩次主修《中山縣志》。1937年春,受當時縣長楊子毅的邀請,他從夏威夷回鄉主修縣志。他遍訪大江南北史學方志專家,與他們磋商志例等問題,並搜集大量文獻,以及各縣志書數十種,以資參考。可惜不及一年,中山淪陷,他遷居香港,仍繼續工作。 之後香港淪陷,修志停止,所徵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諸劫火。 1946年秋,由中山縣參議會建議成立修志辦事處,聘任彼岸為《中山志》主編。1947年,修志納入文獻工作,改為中山縣文獻委員會,彼岸仍任主委。當時文獻會以報紙和刊物兩種形式出版有關中山文史資料。 彼岸對於縣志編纂首訂大要,體例精嚴,紀述側重社會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設類目,以破除歧視婦女的觀念,如有可傳者,只記述懿行才藝,至於節烈異行不宜宣傳;風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跡名勝照片應隨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並釐正前志之訛誤。他認為修志事關重大,不能求之速成,要考證確實。他見識過人,治史嚴謹認真,將重修縣志作為畢生事業,可惜未能完成,成為終生遺憾。 彼岸在濠頭任教時,與村夫、牧童為伍,發掘鄉村歌謠、民諺,如濠頭當時流行的燈棚歌等,在這些歌謠裡去採集活的語言,並創作《新新樂府》,這些詩歌是採擷人民的語言;加以淨化,融合自然的韻律,使之充溢著新鮮活潑的氣息,而其取材是淪陷期間受苦人民的生活實錄。其中最有影響的一篇《走翠薇》,描寫日寇統治區苦鬥的一個小孤女長途負販養母的動人故事。由於詩歌內容真實,充滿樸素的感情,能激起讀者內心的共鳴,一時為之傳誦。 1946年,彼岸對縣當局給他的縣參議員一職,在報上登出啟事,聲明不當,而樂於接受擔任實幹的文獻修志工作。 他樂善好施,扶助弱小。他創辦保育善會,幫助孤苦百姓。他用漂泊美洲20多年血汗掙來的金錢,全部捐助窮苦的人。回國時,除百餘卷書壓囊外,只有兩袖清風。中山淪陷期間,他在家鄉濠頭,生活清苦,但親友、師生遇到困難,他總是有求必應,傾囊相助。中山光復後,石岐鄭氏族人重建祠堂,他利用這個機會,辦起義門小學,專門吸收失學的貧苦兒童,他自任校長,將一個學期應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作為免費學額,讓貧苦兒童有機會讀書。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的威望越來越高,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越來越廣泛,彼岸的思想發生轉變,他拋棄長期的政治信仰,勇於接受真理,逐步成為一個擁護馬克思主義、熱愛共產黨的民主人士。解放前夕,他以高漲的政治熱情堅守崗位,安定民心,勉勵中山修志處和圖書館全體工作人員加強團結,保護文物和所有史料,功不可沒。1949年,中山解放,彼岸轉任中山紀念圖書館館長; 1951年被調到廣東文物保管委員會任職,不久改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他一生致力於文史研究工作,晚年時期一直堅持看書學習,並用北方話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記。[2] 1975年2月2日,彼岸病逝,終年96歲;著有《孫子年考》等書。[1] [1]《鄭彼岸》,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2月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240。 [2]余蘊潔、吳冉彬、徐綺妮:《鄭彼岸先生思想言行初探》,載《中山文史》(第11輯),中山:中山政協,1987,第49-56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更多
尊敬的“澳門記憶”會員,您好!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澳門記憶”文史網的支持與信任。為持續優化會員服務品質與保障會員權益,本網站將自2025年4月28日起正式實施新版的《服務條款》。敬請各位會員詳閱修訂後之條款,有關內容可於以下查閱:
您已詳細閱讀並同意接受該等《服務條款》修訂內容。
若您對本次更新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感謝您一如既往的支持與信任,“澳門記憶”文史網將持續為您提供更安心、便捷的會員服務。
“澳門記憶”文史網 敬啟
發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使用說明
檢視全站索引
“AND”,為縮小檢索範圍,表示前後搜索項之間的 “交集”;
“OR”, 為擴大檢索範圍,表示前後搜索項之間的 “聯集”;
“NOT”,為排除不相關的檢索範圍 ,“AND NOT”表示第二個搜索項,在檢索範圍將被排除。
已經有澳門記憶帳號了? 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