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落老兵扶醉去,斜陽一抹望霞村。
望霞村,即望廈村,此爲清季丘逢甲當年留居澳門,所作之望廈詩也。其寫望廈景色,晚霞一抹,何等詩意!
望廈,又有人稱之爲“旺廈”者,無所取意也。蓋昔日在望廈村聚居者,多屬閩潮人氏,初只寄居,漸且蕃衍,日久成村。但人本有情,總不能忘懷故鄉,因名村曰“望廈”,即取回盼福建、廈門之意也。當年村前之閘門上,有額用草書寫成“望廈”二字,以榜村名,所以史地誌書等,皆沿稱之爲望廈焉。茲據:
《廣東圖説》稱:“恭都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内,有小村三十九,曰前山,曰白石,曰北嶺,曰澳門,曰龍田,曰龍環,曰望廈,曰潭仔,曰過路環,曰橫琴……”
《香山縣圖説》云:“望廈,去城一百三十八里,去寨十八里。”
《香山縣誌》云:“蓮花莖山下,有天妃廟,北麓有馬交石,稍南爲望廈村。”
至於澳葡市政廳編印之《澳門市街名册》則稱:
“望廈村,原日坐落望廈山西南山脚,迨後開闢美副將大馬路時,已取銷,現已不存。”又曰:“望廈,此名係指本市望廈山之南,及西南地區,該區伸展至雅廉訪大馬路附近,即大約由羅若翰神父街起,至文第士街止”云。
望廈處於濠鏡墺北,昔日雖與澳門同在一個半島上,但各固其圉,各自成鄉,澳門稱“澳門街”,望廈則稱“望廈村”焉。早於明朝,我已派有汛兵一營,常屯望廈駐防。清初,更設縣丞分駐望廈村内,以便辦理民夷詞訟。清道光年間,尚同屬中國官吏統治。
據祝淮《香山縣誌》稱:“議者以澳門民蕃日衆,而距縣遼遠,移香山縣丞於前山寨,改爲分防澳門縣丞。乾隆八年,以按察潘思渠,總督策楞,議移縣丞駐望廈村,設海防軍民同知於前山寨,用理猺南澳同知故事……”
張甄陶之《澳門圖誌》又云:“出關閘五里爲望廈村,設縣丞分駐其他,專理民夷詞訟,而統其成於海防軍民同知。”
《澳門紀略》則云:關閘稍南爲望廈村,有縣丞新署。”
所以昔日望廈村内,有汛地街,即縣丞署,及汛兵營所之故址也。自從澳葡開闢馬路,已將該汛地街消毁,併爲現在之美副將大馬路之一部份耳。
對於望廈村内之縣丞署及汛兵營,又據《新修香山縣誌》之紀事篇載云:道光二十九年,葡人毁望廈縣丞署,侵駐拉塔炮台,縣丞遷署前山城内,望廈汛外委退屯白石村三山宫。”
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界址情形疏》亦云:“查望廈汛舊址,即今之汛地街,原設外委一員,駐紥彈壓。道光二十九年,將外委及防兵,遷屯白石三山宫駐防。”
自從道光二十九年沈米事件發生後,望廈村内之中國汛兵及縣丞,迺移屯白石及前山,故望廈村内之防守工事,概由望廈村民自行組織“望廈鄉民知守義團”,負起捍衛社稷責任,在城隍廟址設立團部,士氣昂揚,外人雖驕縱,亦不敢稍越雷池半步也。更因村口有石門一度,可以當關固守,村之週圍,密種竹樹,有如屏幛,村人皆勇敢堅毅,故能保存金甌,以迄於晚清。其間雖經鴉片戰爭,義和團之役,八國聯軍陷京師等等外患時期,難免宵人乘隙覬覦,但望廈村仍能安然獨存者,羣衆之力也。
城隍廟碑記載,兩廣總督張之洞,曾奏禀清帝,盛讚望廈村人:“望廈村民知守義團,團體獨固,深堪嘉尚,不畏時局變遷。戊戌之秋,竟至華洋雜處,余觸目時艱,狂瀾莫挽,不禁感慨系之耳。”蓋至光緒年間,望廈圍竹,忽盡開花,翌年全數凋謝。藩離疏落,遂示人以空虛。加以村中難免有一二敗類,自甘作奸引線,終致大局不可收拾矣。
但村人仍甚倔强,豈肯作順民,雖然《香山縣誌續篇》有云:“查望廈村,民房五百餘家,係光緒九年佔去,添設綠衣館,馬路門牌。”但又有云:“光緒十三年正月,外人逼索望廈等村燈費地租,編列門牌,村人鳴鑼號衆,外人懼,卻走。”所以《中葡外交史》稱:“望廈村一帶地域,至光緒十六年頃,猶屬中國主權,不在澳門範圍之内云”。又據“澳門公牘錄存”中有光緒十六年香山知縣李徵庸上兩廣總督李瀚章禀稿亦稱:“關閘以南之望廈村,均係卑職縣糧户,從未甘向外人交租,在縣控訴有案云”。
昔日澳中有一讖語流行云:“竹樹開花,夷窺望廈。”竟不幸而言中!自從望廈竹圍花後,澳葡迺得入駐望廈。寖且拆閘開路,而石門上之“望廈”匾額,亦被毁滅,只留得村内之城隍廟碑與“望廈村民知守義團”之名共千秋耳。
望廈脱甌後,《百尺樓詩稿》有七言律詩一首詠之云:
“偶從野老識村名,淚漬斑斑尚可徵。一夜嘶風驚戰馬;千門浴血飽饑鷹。鄉民死士唯知義;胡帥亡元亦薄懲。似爲當年留劫火,觀音堂上佛前燈。”
望廈村情況,老居澳門者,尚未易遺忘。現在寶血蚊香工廠背後,尚有矮屋村道,仍留舊觀,儼然小村;美副將大馬路中,還有何氏宗祠,沈氏宗祠等在也。攷何氏宗祠,爲村中之最古者。往日有一俗諺云:“未有望廈村,先有何家祠”由此可知,何氏族人聚居此間,先於沈、趙、許、黃諸姓,遠在望廈建村之前也。望廈村創立自何時,已不可攷。自從閩潮人士移居此間後,生愆日蕃,遂各建宗祠,在此開族,於是蔚然成村矣。
攷望廈村昔日之閘門,大約在今之菲利喇大馬路北端之盡頭處。當民初間,六和自水公司曾在該處,築一水塔,蓋此處井泉清洌,足資飲用,以當時澳中尚未有自來水塘也。殆澳門自來水公司成立發展後,投得專利權,六和水塔迺不得不拆除耳。
昔距望廈閘門不遠,小坵處有奇石兩枚,名公婆石,屼立如人,若夫婦並肩坐,蓋天然生成者也。《澳門紀略》嘗載稱云:“望廈村前二石,每於煙月迷離之際,望若男女比肩立。即之,仍石也。夷人反目於室,出則詣石禳解之,名曰公婆石。”
該石經於澳葡開闢馬路時鑿去,現已不存。至云夫婦反目詣石禳解事,不過傳者故神其説耳。
望廈村傍以南一帶,俱屬農田沼澤,阡陌相望。望廈村民在此耕種,原本藉以謀生者。自澳葡入駐村後,便以賤價將田地收買,填作平原。該處當未闢雅廉訪馬路及未建屋之前,正是一個運動之好場所。一九二六年時,恰逢澳門築港將竣,曾假此場地舉辦澳門實業展覽會。
該會原發起於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始行籌辦。不料各陳列所建築將竣之際,忽遇九月一場颶風。所幸損失不大,卒於該年十一月七日開幕。該會地點在望廈場地,面積約二十英畝。内建陳列所六十處,分飾作中葡英荷之建築型式。展出工商貨品五百九十六種,開展時間經三月之久,統計入場者約共二十九萬人次,爲澳葡繁榮澳門計劃之一次傑作。當時曾出巡遊會景三天,遊龍舞鳳,備極熱鬧。場内更設各種遊藝娛樂,曾將望廈原有之古榕水塘,飾作荷蘭海島之風車磨房,儼然水國風光,塘中出賃舢舨,以娛遊客,極一時之盛也。
在望廈場地,澳葡既於一九二六年舉行過一次“澳門實業展覽會”後,澳門市面繁榮,不免爲之一振,稍現生氣。因之澳葡迺於隔一年,即一九二八年,又在原址,再辦一次“澳門慈善商業賽會”。是次規模宏大,不亞於前次者,且各間陳列館,有用磚瓦結構者,至閉幕後,直可成爲新闢馬路之建築物焉。
攷望廈村自從開闢馬路後,已將舊日不少鄉閭里巷消毁,蓋望廈原有範圍,亦頗不小者,試憶當年望廈村内之街道,計有:旗街、公牛街、媽街、汛地街、北便街、田街、牧羊巷、機杼巷、布巷、永安息巷、蛤巷、青磚巷、草蓆巷、土塊巷、陳巷、云額巷、草蜢巷、養樂圍、杧果圍、帽圍、見小圍、鈕里、手摺里、樹林里、通衢里、田螺里等。又分村爲東西兩約,雖然是小街陋巷,不下有二三十條,現所存者,寥寥無幾耳。
當年望廈村内約有户口五百餘家,雖屬矮屋低簷者多,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亦一安樂之桃源洞也。昔日村中食水用之大井,現尚存在,深湛清冽,稱井泉龍王。該井今在保血蚊香工廠後方,該坊居民尚不少以此井水爲飲用也。井旁有石碑一方,刻有“井泉龍王”四大字,蓋昔日村民迷信,奉以爲井神也。碑之兩傍,更刻有四言聯云:“坎流洊至,井養不窮”斯亦望廈村之遺也。
望廈村民,以何、沈、黃、許、趙諸族人氏爲最多,故前時各姓皆建立宗祠於村内。現尚存在者,有何氏宗祠、沈氏宗祠、黃氏宗祠等,依然如昔也。惟許氏宗祠則於澳葡開闢馬路時,由其族人子孫移遷於關閘外之西瓜埔村中。而趙氏家廟則更早於清朝同治十三年八月間,遭遇一場亘古未有之暴風,全座毁塌,後未建回,現該址遂爲葡兵屯營矣。
何氏宗祠位於觀音古廟不遠。根據俗諺所謂:“未有望廈村,先有何家祠”,可知何氏宗祠爲望廈村中各氏宗祠之最古者,至少亦逾數百年之久矣。該祠曾經多次重修,始能留存至今。查其最近之一次重修,迺在清末宣統三年,歷次修建皆有匾額書明,但惜字跡古舊難辨耳。祠中有顔曰“務本堂”,其兩傍聯云:“自光州固始以來甫,由化郡新安而入詔。”於此叙明其族迺由北南移,更由閩而遷粤也。
聞明宋遺民之何絳,何衡兄弟曾來望廈,駐歇於何氏宗祠。何絳之過澳,汪慵叟有詩詠之曰:“北田高士記陳何,放廢佯狂自嘯歌,爲訪遺臣遊海外,漫天風雨泣銅駝。”並註云:
“何絳字不偕,順德人。布衣好讀書,淹通羣籍。明亡,自放廢,與同里陳恭尹爲澳門之遊。復同渡銅鼓洋,訪逃避諸遺臣於海外。晚與兄衡,及恭尹、陶潢、梁璉隱跡北田,稱北田五子,見《廣東文獻》四集《獨漉堂集》。”
望廈村内昔日之趙家廟,原在觀音堂對方右側,即現在之澳葡兵營處。本屬陸氏故園,清初時讓與趙氏建祠,其不稱宗祠而獨稱家廟者,蓋以趙氏爲宋朝宗室,迺宋太宗趙匡義之後裔也,故其門榜以“趙氏家廟”四字。其門聯云:“譜分玉牒,系本金華。”二門則有長聯云:“溯宋室分封廿七傳,世序相承,源遠流長,有幹有年於茲土;越香山佔籍二百載,宗祊肇造,春霜秋露,以似以續古之人。”道光時進士鮑俊,更爲撰祖先聯云:“迪惟前光,遹追來孝;無忝迺祖,克承厥家。”又據其當年之“趙氏家廟碑記”云:
“蓋聞宗廟可以觀德,祖廟所以本仁。並積德纍仁者,無以垂之於後;非敬宗修族者,無以答乎其先;積善者餘慶,有志者竟成,吾觀於趙氏之作廟,而知之矣。攷趙氏本宋宗室,系出浙江金華浦江縣,其先彦方公宦遊閩粤,作宰香山,遂佔籍焉。傳至英玉祖,始卜居於香邑之澳門,世序相承,以孝友傳其家,詩書世其業,子若孫,皆彬彬秩秩,有都人士風,識者知其德澤之留遺者,遠也。迺家世業儒,素安淡薄,人文蔚起,祠宇闕如。吾友封石無日不懸懸於意中,以艱於財,限於地,又難於經理之得人,故有志而未逮。一日謂其從叔詞卿,及其弟彤階遜夫等曰:吾家自英祖來澳,已歷六傳,先人雖屢擬建祠,而終無成議,寢廟未成,先靈未妥,爲人爲子之道,實有示盡,勳蓄此意已三十年於茲矣。語次惻然,族人感其意之誠,無不鼓舞歡欣,捐資襄事。又幸其弟畫堂深明河洛,理相陰陽,審向背,得望廈陸氏故園一區,乃與叔弟合力營謀,祠基遂定。從此鳩工庀材,經始於庚子之冬,至辛丑臘月告竣,而家廟以成。夫體祖宗未遂之心,成祖宗未竟之事,非封石仁孝性成,鬱積於中,有以咸孚乎宗廟;而族人復能讀書明理,深知乎木本水源之義者,何以一德一心,相與有成若是哉!和氣積而家道興,根本立而枝葉茂,吾知斯廟之作,展禴詞丞嘗之禮,講冠昏之儀,孝弟之心油然以生,仁讓之風勃然而起,將見以道德而發爲文章,以文章抒爲經濟,於以黼黻皇猷,光昭世德,以爲本邑生色者,正未有艾也。後之登斯堂者,想先世積纍之隆興,後嗣繼述之善,而知百計經營以成此堂構者,其來有自也。予不文,因詞卿之請而不獲辭,即事之始末紀之,勒諸瑣珉,以垂奕禩。戊辰科舉人梁尚舉頓首拜撰。”
溯望廈村趙氏之定居,迺源於明初洪武十九年,趙彦方作宰香山,卒於任内,其後人遂佔籍焉。傳至明末崇禎十五年,趙英玉始卜居澳門。更歷六傳而至趙封石,迺建趙氏家廟於望廈,由是子孫世續,書禮傳家。在科舉時期,代有中式者,如趙元輅及趙允菁,父子先後同中舉人。據《香山縣誌》載稱:“趙元輅,望廈人,字任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第十八名舉人。”又稱:“趙允菁,望廈人,字孔堅,嘉慶六年辛酉科第四名舉人,授南雄州始興縣訓導。”故昔日在望廈趙氏家廟内,懸有“父子登科”之匾額一個。同治十三年八月大風災,趙氏家廟被毁後,該匾由其後人保存,現尚懸諸趙家圍之趙瑞春堂大屋中也。
攷趙元輅,字任臣,號九衢。生於乾隆巳未四年,例授文林郎,覃恩貤贈職郎。以府案首入泮,補廪膳生,乾隆丁酉科中式,廣東鄉試第十八名舉人,著有“觀我集”。於乾隆庚子四十五年三月,以會試卒於京師廣州會館,時年四十二歲,迺宋太宗趙匡義之第二十世傳孫也。
趙允菁,字孔堅,號筠如,趙元輅之長子。生於乾隆戊子卅三年,例授文林郎,覃恩勅授修職郎。嘉慶辛酉科中式,廣東鄉試第四名舉人。道光丙戌鄉科會試後,大挑二等,授南雄始興以教諭銜,管訓導事。越二載,李鴻賓制憲謂其足爲文士楷模,調委越華監院。邑人士聯名請仍留學任,以培士氣而勵人材。癸巳年陞授平州學正,改授京職,籤授翰林院典簿,著有《書澤堂文稿》行世。其門人多是當時俊彦,如招子庸,曾望顔等。回憶其卒於道光甲午十四年時,享壽六十七歲,其門人曾望顔太史有聯輓之云:
“憶馬帳追隨,道德文章,遠大相期,正思義盡恩深,三十年來猶昨日;記羊城叩别,燕台粤海,音書不斷,何意星沉月落,七千里外哭停云。”
望廈村民,除何、趙、沈、黃、許各族建有宗祠外,村内尚有許多他姓人氏留居,如陳、鄭、韋、楊等,皆爲鄰近鄉人流落是間,而在此開族者,數代相傳,儼然成爲土著矣。
昔日科舉時代,村中各氏子弟皆以爭取功名爲閭里光,如趙元輅及趙允菁之父子登科,固在望廈村中一時傳爲佳話;其他各姓弟子中,亦有奮發而能青一襟者,如陳景華是也。
陳景華,字鹿畦,别號無恙,望廈村中子弟也。晚清光緒十四年戊子科,獲中第十五名舉人。曾任廣西貴縣知縣,秉性剛直,廉潔無私,嚴明勤政,有幹吏之稱。因其嫉惡如仇,以故殺當時之巨匪陸亞發,招致兩廣總督岑春煊之忌,遂逃走暹羅,從事排滿革命工作。至辛亥革命後,即任廣州市警察廳長,其政績最燴炙人口者有二:一是捕殺擾亂廣州治安之百二友及其他流氓匪類,使地方爲之寧靜;一是創辦廣東女子教育院,使廣州市内之婢女、妾侍、尼姑、娼妓等都可以得到申訴,脱離虐待而得受教育也。獨惜陳執政不久,民國二次革命失敗,革命黨人多逃亡海外,陳恃自己正直無私,卒被龍濟光誣殺。時爲民國二年九月十六晚之中秋夜,龍假意派人請陳到督府賞月,陳坦然赴約,致被陷害。陳死後,移葬香港咖啡園,其墓碑銘刻道:
“强項之令,猛以濟寬。冤同三字,獄等覆盆。蓋棺定論,毅力維新。哀我民國,喪此良人。”
昔望廈村在濠鏡墺,孤懸海隅,遠離滿清統治,故明末志士,前代遺臣,多遁跡斯土,且作寓賢。如方顓愷,屈翁山等,更托身空門,寄居普濟禪院。汪兆鏞之《澳門雜詩》,有詠方顓愷七言絕句云:
“咸陟遺堂莫可尋,宗風衰歇悵而今。山河悟徹微塵耳,但得安居便死心。”
蓋方顓愷於明朝亡後,削髮爲僧,誓死不仕,字跡删,著有《咸陟堂詩文集》。其《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詩云:
“但得安居便死心,寫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鴂音。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身縱步吟。”
攷跡删曾於一六三七年丁丑之夏,移錫望廈村之普濟禪院。其傳見《番禺縣誌》云:
“方顓愷,字趾麐,隆武時補諸生。平靖二王入廣州,督學使者檄諸生,不到試者以叛逆論。顓愷誓死不赴,削髮爲僧,名光鷲,字跡删,後易名成鷲,躬耕羅浮。母殁奔喪,饘粥苫凷,一遵儒禮,葬日負土築墳,痛哭而後别。俗僧笑之,弗顧也。晚年掩關大通寺。康熙元年壬寅,年八十六卒。著有咸陟堂文集十七卷,詩集十五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指十卷,金剛經直説一卷,道德經直説二卷,註莊子内篇一卷,鼎湖山誌八卷。”
其遺墨多署跡删,現藏望廈普濟禪院者有草書條屏。
望廈之寓賢,昔有方顓愷外,還有屈翁山。蓋屈翁山亦明末志士也。忽儒忽憎,以隱以逃,與望廈普濟禪院之開山祖大汕法師極友善,故嘗在康熙二十七年居此。
攷屈翁山,粤人,初名紹隆,翁山其字也,又字介子。明諸生,遭亂棄去,禮天然和尚爲弟子,釋名今種,字一靈,一字騷餘。中年返儒服,更名大均,以詩文名世,與陳恭尹,梁佩闌稱嶺南三大家。著有《翁山詩略》、《翁山詩外》《翁山文外》、《廣東新語》、《四書補註》、《皇明四朝成仁錄》等書,觸犯清廷,多被削版。其《廣東新語》内,有《澳門記》,紀述頗詳。《翁山詩略》有詠澳門五言律詩六首云:
“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兵愁蠻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
“南北雙環内,諸番盡住樓。薔薇蠻婦手,茉莉漢人頭。香火歸天主,錢刀在女流。築城形勢固,全粤有餘憂。
“路自香山下,蓮莖一道長。水高將出舶,風順欲開洋。魚眼雙輪日,鰍身十里牆,蠻王孤島裡 ,交易首諸香。
“禮拜三巴寺,番官是法王。花襔紅鬼子,寶鬘白蠻娘。鸚鵡含春思,鯨鯢吐夜光。銀錢么鳳買,十字備圓方。
“山頭銅銃大,海畔鐵牆高。一日番商據,千年漢將勞。人惟真白㲲,國是大紅毛。來往風帆便,如山踔海濤。
“五月飄洋候,辭沙肉米沉。窺船千里鏡,定路一盤針。鬼哭三沙慘,魚飛十里險。夜來鹹火滿,朵朵上衣襟。”
望廈村,雖屬窮鄉陋巷,但昔日不乏名人奇士,棲隱其間,或以普濟禪院作居停,如跡删,今種輩會錫寺中,前文已約言之矣。又聞明末清初之廣東愛國詩人陳恭尹,亦嘗寄居望廈村焉。故清朝光緒九年進士丁仁長,有五言詩二首云:
“本是蛟鼉窟,翻棲猿鶴羣,天方賚幽隱,世不厭風雲,畫老從仙得,琴清許佛聞,最憐三宿地,海月白紛紛。”
“荷闌豐草院,昔我亦停車,欲訪天然宇,來尋獨漉家,萍蓬似孤嶼,天地一枯楂,賸折芳馨贈,春勝菊自花。”
蓋獨漉迺陳恭尹號,言來望廈訪其故居也。
攷陳恭尹,字元孝,自號獨漉子,爲明季吾粤三大忠臣陳邦彦之長子。陳邦彦殉難時,恭尹才十七歲,承增城義士湛粹相救,迺得保存忠良遺孤,並以次女妻之。陳恭尹對於清朝,終生不仕,自稱羅浮布衣,精書法,工詩文,與當時之屈翁山,及梁佩闌,會稱嶺南三大家,恭尹且爲之冠。晚年隱居北田,又與何絳,何衡,梁璉,陶璜等共稱北田五子。壯時,嘗與何絳來居望廈,復同渡銅鼓洋,訪明末諸遺臣於海外,且與望廈普濟院之開山祖師大汕和尚極友善,著有《獨漉堂詩文集》。其遺品,有草書條屏,現藏普濟禪院中。
望廈普濟禪院之開山祖大汕和尚,本亦明末遺民,托禪而隱者,故屈翁山、陳獨漉等來望廈,與之最友善,蓋以其志同道合也。
攷大汕和尚,字石濂,號廠翁,自稱是當時名僧覺浪杖人道盛之法嗣。嘗錫廣州長壽寺,又曾至安南爲國王求雨而得甘霖,厚獲而歸。迺大修長壽寺,來望廈營建普濟禪院,到清遠築峽山寺,是以普濟禪院之祖師堂内有聯云:“長壽智燈傳普濟,峽山明月照蓮峰。”中奉大汕自繪法像,作披髮頭陀狀,足見其不肯剃髮,不侍清廷也。大汕不泥佛誡,不戒綺語,好談兵法及當世之務,廣交遊,工詩善畫,百藝無所不能,著有《海外紀事》六卷、《濃夢尋歡》竹枝詞卷,《離六堂集》十二卷。
易堂九子中曾燦,有《離六堂集序》,其言大汕和尚云:
“……和尚爲吾鄉九江人,少事浮屠,足跡幾遍天下。好爲詩歌,深得風雅推騷刺之旨。嘗與之談當世之務,娓娓不倦,蓋其天文地理兵法象數,以及書畫諸子百家之技,無不貫通其源委……今和尚之爲人,豈與枯寂浮屠同日而語乎,抑有托而逃者耶?當其狂歌裂眥,淋灕下筆之時,懷抱淵源,空今曠古,此其志豈小哉!然和尚之善藏秒用,又未知其涯矣。”
於此可知大汕之抱負,不同凡僧,惜卒招清吏之忌,下其於獄,在破解回籍途中而殞命耳。
在穗之商愆鎏太史昔遊普濟禪院,有詠石濂頭陀畫像云:
“石濂交際徧名流,工畫能詩孰與儔,長壽寺門朝市改,低徊小像幾春秋。”
望廈村自昔與澳門街毗連,交通較便,士大夫來此。以其仍屬華人統治,多愛在望廈駐留。且村中有普濟禪院,地方軒敞雅潔,騷人畫客,每擇斯以聯壇結社、廣交文字因緣,誠望廈村之勝事也。如嘉道時,黃培芳及鮑逸卿等輩,曾在寺中組織詩社焉。
攷黃培芳,字子實,一字香石,香山人。迺瓊州教授紹統之子,嘉慶甲子科副貢,歷任乳源訓導,武英殿校錄,晋中書,一時碩彦多出其門下。如許乃晋尚書,羅文俊侍郎,林召棠殿撰等,皆屬其弟子也。培芳工詩善畫,與當時番禺之張維屏,陽春之譚敬昭,合稱爲粤東三子。
道光辛壬間,被委襄治夷務,嘗來望廈,與進士鮑俊極友善,結詩社於普濟禪院中,一時唱和之聲,如漱珠唾玉,澳中文風爲之一振。至咸豐丁巳,時巳年登八十,尚重遊泮水,學者稱之爲粤嶽先生。著有《易宗》、《浮山小誌》、《云泉隨扎》、《虎坊雜識》、《縹緗雜錄》、《藤陰小記》、《嶺海樓詩文鈔》、《香石詩話》等,善畫山水,法九龍山人。
鮑俊,香山場人,字宗垣,號逸卿,道光三年癸未進士翰林院庶士,改刑部主事,候補郎中。工詩詞,精書法,善畫梅竹,求書者接踵,潤筆所入,特構榕塘。其鄉有石溪,崖峭瀑奇,幽棲其中,自號石谿生。晚年主講鳳山豐湖書院。著有《榕堂詩鈔》、《倚霞閣詞鈔》。一八四九年澳門之沈米事件,實其主使者也。
望廈村,昔日既有詩社,又有畫壇。詩人畫客,蔚然薈粹於望廈之普濟禪院中。文藝之盛,至今猶爲人所樂道。法書名畫現藏寺中者,皆足爲人所珍惜也。
如嘉道年間,謝蘭生曾來望廈,在普濟禪院内之妙香堂,雅闢畫壇。一時之騷人畫客,如其弟謝觀生及孝廉鍾啓韶等都惠然肯來,羣賢畢集,爲望廈增色不少。
蓋鍾啓韶於道光時來澳,題有《澳門雜詩》十二首,其中有句云:“思憑謝公筆,圖畫貯滕。”並自註云:“謝退谷偕行善畫。”
攷謝蘭生,字佩士,號澧浦,又號里甫,别號里道人,南海人也。嘉慶七年成進士,旋選翰林院庶吉士。迭主粤秀,越華、端溪講席,後爲羊城書院掌教。當兩廣總督阮元重修《廣東通誌》時,延任總纂。爲古文得韓、蘇家法,書學顔、褚,書法董、吴,著有“書畫題跋”二卷,《常惺惺齋文集》四卷,《詩集》四卷,《北遊紀略》二卷,《遊羅浮日記》一卷。其弟謝觀生,字退谷,號五羊散人,亦以繪事稱。與其兄蘭生齊名,時稱二謝。
謝蘭生於嘉慶十三年,曾爲望廈普濟禪院之妙香堂書一匾額,題有“妙香”二字,並序述畫壇事。後來該妙香堂,又爲嶺南畫派之高劍父師生輩,作爲研究畫藝雅集之所。
望廈村之文風,以清朝嘉道間爲最盛,詩文書畫,都有名人騷客爲之倡。蓋當時之俊彦耆宿,達官貴人等,都常臨駐息,或來此辦公,或道經暫歇,鞭絲帽影,遺墨留題,已屬不鮮;況且村中之文士輩出,如趙元輅父子登科,陳景華中舉等,皆爲村人所矜道者也。曾望顔太史少時,亦曾隨父來此遊學,在望廈趙允菁門下受業。後來一舉成名,授翰林院編修,還常回鄉,道經澳門。咸豐時,嘗爲望廈重修普濟禪院碑記書丹;同治時,又爲《澳門創建康真君廟碑誌》撰記,其記中有云:
“濠鏡又名海鏡,左有天后宫,右有蓮峰廟,帶海襟山,華夷雜處,蓋邑南之勝境也。余少時,嘗從光大夫遊學於茲。通籍後,歷宦京外,遥别故鄉者,三十餘年矣。”
攷曾望顔,字瞻孔,號卓如,香山人也。嘉慶二十四年舉人,道光二年進士,翰林院編修,轉御史,遷順天府尹。纍擢陜西巡撫,四川總督,以事劾,罷免。旋被召入都,授内閣待讀學士,乞歸。
其生平居官清介,有惠政。光緒六年,陝西總督左宗棠,奏請於陝西省城建立專祠,並將政績,宣付史館立傳報可。善畫蘭石,極秀勁有政,世人咸寶之,見汪兆鏞之《嶺南畫徵略》。
道光二十四年夏,中西貴要,均到望廈,商訂所謂中美互惠商約,即後來之望廈條約是也。
當時清廷正在鴉片戰爭敗績之後,與英國議和,訂立南京條約。美國見而垂涎,特派出節使冠興Caleb Cushing來華,本欲覲見道光皇帝,實行以武力要脅訂約,以攙取中國利益。但清廷不欲其來京面談,特委其皇族親信耆英,爲與美國治商之全權大臣,並即派遣布政使黃恩彤先來澳門望廈,阻止美使北上,故後有在望廈簽約之舉。
望廈條約,迺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五月十八日,即公元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在望廈普濟禪院内小花園之石圓檯上簽定者。清廷方面代表爲當時兩廣總督耆英,兩位布政使黃恩彤及潘仕成充任參贊,偕同趙長齡侍御、銅竹樵司馬等,辦理此事,駐節望廈將旬,公畢然後返穗。美國方面代表爲美國特使冠興,美艦隊提督柏架氏竟作威脅式列席,由最初來華傳教馬禮遜教士之子儒翰馬禮遜任通譯。此一喪權辱國之條約,雖美其名爲中美互惠商約,其實絕不平等互惠,迺在普濟禪院簽訂,有污佛門善旨。現石檯石凳仍然存在,商愆鎏探花曾有詩詠之云:
“國耻百年湔不盡,猶留石案任摩挲。侵陵外侮通商始,貧困由來血淚多。”
攷一八四四年代表清廷來望廈,與美國簽訂望廈條約之耆英,原迺滿清皇室,滿洲人,别字介春。道光鴉片戰役,英艦擾江寧時,耆英正充杭州將軍,統握兵符。惜其素來愚懦懼外,所以敗績求和,曾赴南京與英商訂五口通商條約。偷愛偏安之清廷,反以其議和有功,旋授任兩廣總督。無奈當時廣州民衆,堅决反對和約,抗止英兵入城,並有三元里之役。耆英遂不得已乞請内召回京,曾任文淵閣大學士。
當其與英簽訂南京條約時,美國見獵心喜,迺有特派大使來華,要求訂約之舉。美使本擬親謁道光皇帝,但清廷避免面議,授命耆英赴澳與之接洽。事前耆英曾發快信三封,並派黃恩彤先來望廈,阻止美使北上。至六月中旬,耆英始抵望廈,由十八日開始酌議,經過兩星期磋商,先由美方起草,三天内完成後,稍將部份細節修改,大部依照草約訂定,遂於七月三日雙方簽署。該約共有四本,分用中、英文字繕寫,合共三十四款。聞當時約内文字之錯桀謬誤處,竟達二百餘點之多。
耆英於簽約後,翌日即離望廈返穗。又兩月,在黃埔與法使訂中法修好條約。後來更與挪威、瑞士等國立約。統觀耆英經手所訂之條約,無非都是喪權辱國者。
至一八五八年,英法兩軍又入天津,耆英奉召赴天津議和,但以庸絀無能,難於應付英、法要求,無法修改初期經手之條約,迫得懼逃回京。清廷卒以其有虧職責,勅令自盡而死,此即經手簽訂望廈條約者收場也。
商訂望廈條約時,清廷耆英曾偕黃恩彤及潘仕成兩位參贊到望廈來。
黃恩彤,寧陽人,别字石琴,道光初年進士,官至廣東布政使。當美使來華請訂商約未到埗前,先由美國駐粤領事通知廣州政府,謂美使將逕由天津直詣北京面帝。廣東總督程矞彩未肯答允,只許代奏京師,故受命代表清廷議約之耆英知悉,立即派遣廣東布政使黃恩彤趕來望廈,阻止美使北上。此行果然成功,頗獲清廷嘉賞,黃恩彤因得賞戴花翎一枝。及耆英來澳,黃恩彤充任參贊,公畢返穗後,翌年擢升巡撫,旋又因事革職。聞咸豐年間,捻軍攻山東,恩彤適在籍,獻議築壘掘壕,建炮台以固守,捻軍無所得食,致漸窮蹙敗退云。
潘仕成,廣東番禺人,别字德畲,爲廣州首富,賞布政使銜。因以洋務辦鹽起家,多與外人往來,故商訂望廈條約時,耆英挽其偕來,與黃恩彤同當參贊,襄助訂約。公畢,嘗同遊媽閣,泐石留念。刻云:
“甲辰仲夏,隨侍宫保耆介春制軍,於役澳門。偶偕黃石琴方伯,暨諸君子同遊媽閣,題此。番禺潘仕成。”
潘仕成雅愛結交文士,嘗建海山仙館於羊城,時作詩酒之會。刊有海山仙館叢書,海山仙館法帖等。後因税務事件,卒被查封。
望廈條約之美方簽署代表人──寇興(又譯顧盛,Cushing, Caleb),本迺美國法律界中人,嘗任馬薩諸塞州議員。其父曾來中國經商,其兄弟亦在廣州致富,原是一個來華販毒世家。冠興幼即狡黠;極聰穎,及長,能通多國語言,且能説中國國語,對中國之歷史、風俗及貿易習慣等,皆曾致力研究,爲一位“中國通”人物。一八四二年時,寇興在華盛頓國會會議席上,曾極力提出要調查與中國貿易之狀況,並擬派遣特别代表團來華,與中國締結商約。其建議於是年底獲得美國國會年會通過,撥助四萬元作爲出發資金。
一八四三年五月,寇興被委爲第一任美國對華外交團團長,暨美國駐華外交特派員與公使全權代表,遂於八月五日,領着四艘美國海軍艦隊出發來華。啓行時,其帶有當時美國國務卿韋氏 (Danial Webster)之訓令,及美國總統泰萊 (Tyler) 之親筆致道光皇帝函件及禮品。
來華之四艘美艦計爲:旗艦米蘇里號,拔蘭地號,梨酒號,及聖路意士號,當各艘艦隻橫渡大西洋,至直布羅陀海峽時,米蘇里艦不慎失火焚燬。寇興迺改以拔蘭地艦作爲座駕艦,遂於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抵達澳門。
寇興來華前,嘗誇口必要親見道光皇帝,使美國取得與英國在華同等利益,孰料被耆英所阻,不得不於七月三日在望廈簽訂所謂中美互惠商約。迨其返國後,聲譽大振,晚年還出任美國之律政司,聞其對駐華之領事裁判權,尚懷叵測云。
望廈村後,有蓮峰山,爲村之屏障;東南盡處爲蚧崗,有蟹眼石,普濟禪院座其前;蓮峰中部垂一脈,石托天然,爲燕子巢,故稱燕嶺,觀音古廟築其下。昔吴應揚太史曾遊至此,闢爲勝地,嘗爲觀音古廟修撰碑志,且自述云:
“予髫齡時,聞澳門望廈鄉有蓮峰,未之至也。及長,由穗城歸里,路經關閘沙,始知爲蓮莖。莖盡矗起一山,即向所聞之蓮峰也。余攀躋而上,見龍勢直走,中復垂一脈,石托天然,俗呼爲燕子巢,又曰燕嶺。”
所以望廈,昔人謂其爲蚧地,或稱之爲燕嶺。但自澳葡在望廈鑿山闢路後,蚧蓋爲之破碎,燕巢爲之傾倒,無復舊觀耳。
攷吴應揚,號星樓,恭都翠薇人。清同治壬戌舉人,戊辰成進士,改刑部主事,升員外郎。辭職歸里,主講豐山書院,教士先氣節而後文藝。遇親友之喪,雖遠必吊;遇貧者,更厚賻之。疏財好義,晚年迺家貧,其處之泰然。與兩廣總督張人駿爲同年,張極重之。曾代河南鷄春岡民十六人昭雪冤獄,是以人皆德之。享壽八十餘歲而卒。見《香山縣誌續編‧列傳》。
望廈村内之廟宇,相傳以觀音古廟爲最古,大約始自明朝中葉。其他如普濟禪院,則鼎建於明末天啓七年。康真君廟及先鋒廟,則大約建自清朝道光年間。而福德祠及武帝廟,迺於清光緒卅三年由龍田遷來者。至於城隍廟,則爲光緒卅四年,由觀音古廟傍座擴建者也。
望廈之東廓,有墳場焉,稱“望廈墳場”,或名“新西洋墳場”。昔爲村外園地,其北高地舊有基督教墳場,中有廿穴石墓,迺十八世紀時期散葬於澳城牆之外人骨殖,後來遷移叢葬於是者。其下之新西洋墳場,迺因抗戰時日人封鎖關閘,棺柩不能出閘安葬,故澳葡遂闢此場地以補舊西洋墳場之不足也。抗戰後之同胞身死者,仍多埋葬此地,如國畫大師高劍父身後亦瘞於斯也。
攷高劍父,名崙,番禺圓岡鄉人。據其七十歲自述謂:原生於小康之家,誕時適爲凶日,家人以其不祥,且屬庶出而遭蔑視,幾擬棄送嬰堂,賴父不忍迺得留養。十一歲,雙親見背,家遂中落。初依兄種田爲生,後執役於族叔醫館。叔精醫及善繪,暇輒授以繪事,美術興趣由此啓迪。
十四歲,返河南兄家,得族兄之介,獲免費師侍名畫家居古泉門下,雖每日往返十數里至隔山鄉就學,弗以爲苦也。同門中有伍德彝者藏畫甚富,故忍辱叩拜執弟子禮,得其示看,並介紹參觀粤中收藏家如潘仕成、吴榮光、張蔭垣、孔廣陶等之珍藏書畫,臨摹揣摩,盡窺其秘。後更從法人麥拉氏習西洋畫,時因經濟困難,迫得出任圖畫教員。
旋積資東渡深造。時年十八,考入日本東京美術學院。在日得識孫中山先生,遂加入同盟會,後被派回粤實行革命工作,凡八年,歷次舉義及暗殺事,皆躬與其間。
迨民國成立,棄功不居,仍舊潜心作畫,創辦嶺南春睡畫院,傳授弟子,一時稱其畫爲嶺南折衷派。一九三零年,週遊印度、緬甸、錫蘭、不丹、尼泊爾、波斯、埃及等地,藝名日彰。
抗戰期間來澳,隱居望廈普濟禪院,日與弟子等研畫於妙香堂。和平後返穗,創辦廣州高中美術學院。翌年,任廣州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一九五一年,卒於澳門,時年七十三,葬於望廈墳場。
關聯資料
更新日期:2019/0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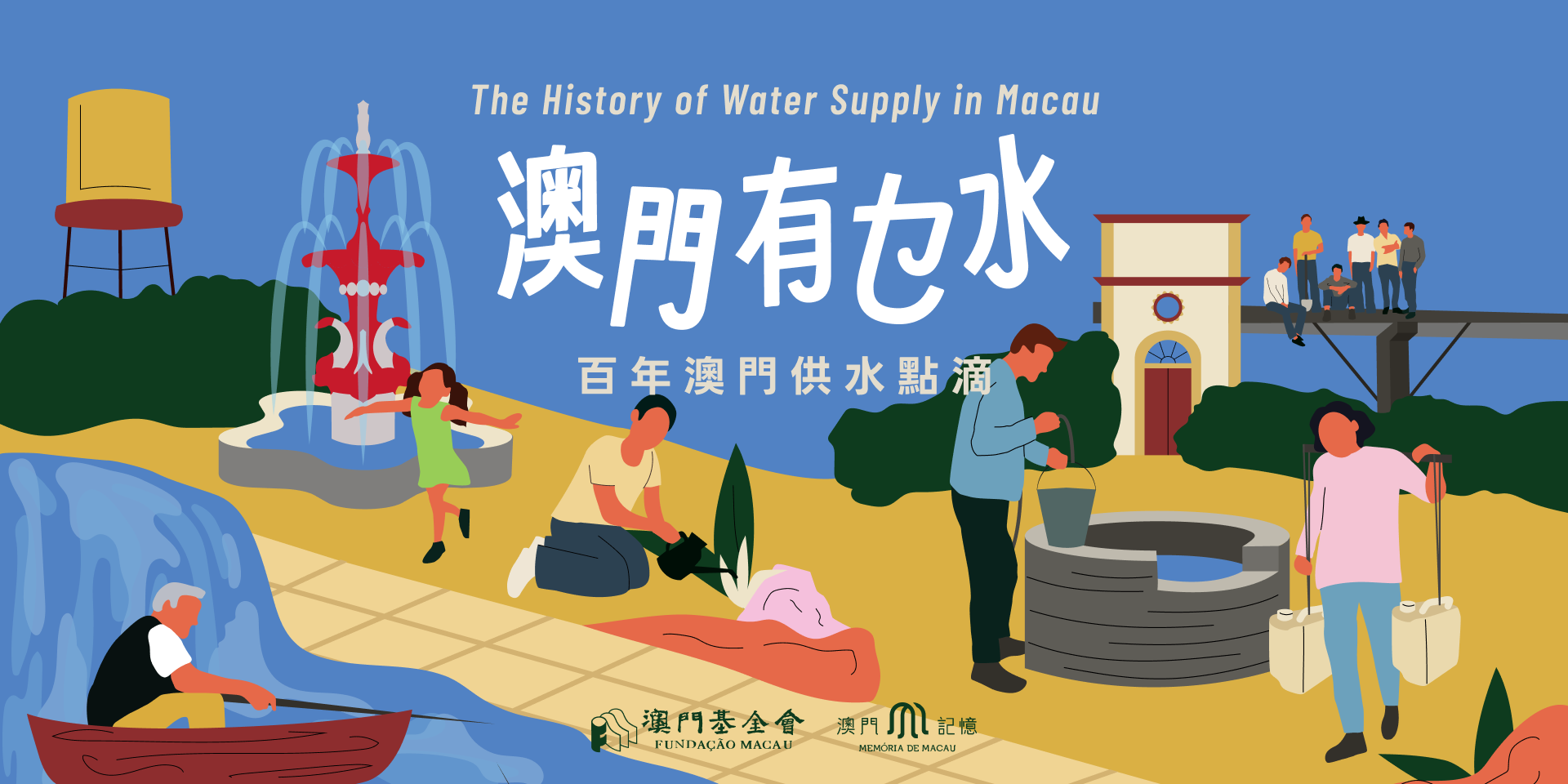
留言
留言( 0 人參與, 0 條留言):期待您提供史料和真實故事,共同填補歷史空白!(150字以內)